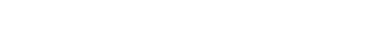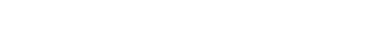“如果中午不急着回去,不谢绝矿方的挽留,如果他们不急刹车滑行20多米,如果再快几秒或者再慢几秒,侧面的渣土车就不会朝着副驾驶室直撞过来。”
沈华军告诉我的时候心情极其沉重,充满了不解、遗憾和悲痛,但是已经没有“如果”了,2012年12月7日近午时分,一声惨烈的撞击,靳祥生没有闯过他人生的这个“十字路口”。
农历2012年腊月20日,靳祥生去世后第52天,我冒雨来到他生前工作的单位中煤矿建淮南工程处采访。到淮南已是下午四点半,下车时扑面的冷雨悲切而凄凉。
“这是昨天刚寄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他的事迹报道在国家级文学刊物发表了。”我第一位见到的是该处党群部部长程晋舜,他递给我一本沉甸甸的刊物,并向我介绍了靳祥生的事情,“《安徽工人日报》《淮南日报》都在头版头条进行了重点报道。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士兵专门派人远赴内蒙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追思会,并要求在全集团范围内开展深入学习活动。”
靳祥生于1979年12月30日出生在安徽萧县农村,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2004年9月进入淮南工程处工作。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毕业生,他的事迹何以引起这么大的动静?带着这些困惑,我进行了3天的采访。
“又来了一名电焊工”
“又来了一名电焊工!”党群部副部长胡矿礼在2004年10月一次去刘庄工地时,看到了一名英俊高大的小伙子在进行焊接工作,他对同行的人说。
项目部的人给他纠正“那是我们刚招来的大学生,我们告诉过他搞技术学管理不用学这个,但是他还是主动要求学习”。
8年了,胡矿礼还是十分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感受:“2004年,本科生在我们野外施工单位还是凤毛麟角,肯来就不错了,来一个都是领导的宝贝疙瘩,倍加呵护,哪有干电焊的?腰酸背痛苦累不说,就单单眼睛流泪就让初学者受不了。”
刘庄项目部是靳祥生工作的第一个工地,在那里他把电焊工、电工、安装工、钻工都一一学习过。仅仅几个月,他就担任了项目部冻结站副站长。
据职工介绍,安装设备期间他一般会提前去上班,或者晚饭后去站里看看,对照专业书籍和图纸,想想下一步应该如何下尺寸、下料、对接管路等等,然后把需要下的尺寸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到第二天下尺寸时直接按照本子上的类别,对号入座填测量或计算数据。“我干活有点慢,所以就把能提前做的先做了”,别人喊他喝酒、打牌、散步,他常以这个借口推辞。
很多职工反映,他认了很多师傅,不挂名的就有几位。一位“师傅”反映,“他不懂的就追着你问,要是你忙,怕耽误工作影响效率或者认为他没必要学而不教他时,他就会硬缠着你,紧追不舍。”
时任口孜东项目部总工程师王峰的回忆进一步作了验证,“2007年,靳祥生尽管已经是工程部部长了,还经常缠着我追问问题,有一次趁我上厕所时,他把我堵在了厕所门口,问了半小时还不肯罢休,我说坐下聊吧,我俩就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直到有几位女同志老是看着我们时,才意识到坐到了女厕所门口……”想起这件事,王峰以前总是当作笑话讲,“现在才发现,再也没有遇到像他这么爱学的人了!”
顺便介绍下,口孜东煤矿矿井深度达到737米,是当时国内井压最大、表土最厚、冻结壁最厚、地质条件最复杂的冻结井筒,号称“亚洲第一井”。在难度这么大的情况下,淮南工程处的领导毅然决定让“工龄一年多”的靳祥生负责技术施工,足见领导集体对他的信任。
“一起买的鞋,我能穿他三双”, 靳祥生的大学同学,也是他的同事李子祥回忆说,“口孜东冻结站房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制冷中心”,24组设备摆放长度达到150米,机器运转时,靳祥生很少歇脚地来回巡视运转数据,他穿的鞋很快就烂了。”
还是在口孜东,据王春彤介绍,由于项目部采用了安徽理工大学专门研发的光纤测温技术,相对传统的测温设备,实现了数据实时反馈,更加智能化,对于这项全新的技术,靳祥生天天跟着教授学,寸步不离,最终熟练掌握了这一新设备,《光纤测温技术的革新与应用》作为一项小革新,荣获了集团“五小成果二等奖”。
“小靳对未知领域总是有着很强的探索欲”,和靳祥生同年参加工作,现任淮南处的兄弟单位淮北冻结处副总工程师的刘亚军回忆起一件事,“2007年,公司组织我们4人参加‘压力管道设计许可证’学习,我们都是第一次接触,没人懂,从合肥专门请来的一位姓黄的教授给我们上课,靳祥生经常询问老师问题,上网查资料,他学的最快、认真,掌握的最熟练,刻苦钻研的劲让人佩服。”
夏天穿着棉袄干活
本文中多次提到的“冻结”就是通过人工作业使井筒周围土层冻结硬化,以阻挡流水流沙影响掘进。在井口地面上挖出一个距地面3米的地下室当做沟槽,用来测量温度。
口孜东煤矿是2007年6月份开挖的,阜阳夏天最高的温度高达38-39度,而地下沟槽的温度却只有零下十几度,冰火两重天。
“真的穿棉袄吗,还在里面一干就是三天?”,见到以前有报道这样说,我以怀疑的态度询问王峰。
“给你算个账吧,有一次我们要把158个输送冷量的冻结孔全部测一遍温度,每个孔顺利的话要1个小时,没有几天时间根本测不出来,不穿棉袄怎么行?”王峰还进一步补充,“为了方便工作,靳祥生还把桌椅都搬到地下沟槽里,一边测量,一边记录,一边分析。”
“还有比这更困难的呢”,现在已是技术副总的李子祥说,“还需要到井筒的掘进面测量温度,地下六七百米深的地方温度只有零下10度,每天都要穿棉袄下井,在几平米的狭小的空间里待几个小时。”
“这样的日常工作普通职工完成不就行了吗?”
“论说他不应该去,技术员、井长、副部长,靳祥生手下有四五个人,三班倒都排的开,但是他有一个习惯,什么事都自己上,他要掌握第一手资料”。
“有一件事当时我们都有意见,冻了几个小时刚上来,发现一个数据出了问题,他非要立刻再下去一次,中午饭都不吃了。”作为老同学似乎有点底气,李子祥认为“我们还是凑掘井单位的吊罐才能上下,在下面待多长时间根本没个准。”
“他告诉我们,细小的疏忽都有可能酿成大事故,甚至导致整个工程毁于一旦。幸亏我们重新下井,发现并及时排除了施工隐患。”
做技术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和侥幸,需要细致周密的态度。在板集项目部,他担任项目部副经理,分管技术工作,他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对技术管理工作的要求:“根据技术数据,每天进行分析,每十天召开一次小的技术分析会,邀请甲方、监理、工程处专家参加,每一个月召开一次大的技术分析会,邀请国内知名专家。”
“要与公司共成长,我相信,如果愿意承担成长的责任,那么就会获得成长的权利。”靳祥生在最后一篇文章《与企业一起成长》中提到了“责任”,生命需要成长,责任需要担当。能够承担责任,靠的是勇气,展示的是自信,激发的是动力,收获的是成功。
《737m冻结施工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应用》的项目研发中,靳祥生主要负责现场实施及数据收集分析,该项目荣获安徽省和淮北市科技进步奖,参与《737m超深冻结钻孔偏斜质量控制》QC小组,荣获“2011年全国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称号,他参与的《国投新集口孜东主井井筒冻结及掘砌工程》在2011年获“全国煤炭行业优质工程”称号。为他申报的另一项省级荣誉待批中……
“下一次就轮到你了”
杨村项目部会议室里张贴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2007年,靳祥生的师傅宋宏生为即将参加淮北市劳动模范颁奖仪式的王春彤佩戴大红花,穿着红T恤的靳祥生含笑站在一旁,但是他的表情明显的流露出羡慕和憧憬。
为了验证猜测,我专门采访了王春彤。“我们俩确实聊过一次,见他很羡慕,我开玩笑的说:‘下次劳模就轮到你了’。”经过这次鼓励,他干劲更足了。
五年后,靳祥生去世的前几天,为他申报的安徽省煤炭工业系统劳动模范刚获批,但是他没有机会披红挂彩了。“本来我想为他也戴一次红花,让他当主角体验下……”他的年近花甲的师傅,板集项目部经理宋宏生老泪纵横地说。
八年来,他获得的荣誉,从国家级、省部级到市级,打印出来竟有一页半A4纸。荣誉是一种奖励,而他却把追求荣誉的过程当作激励。难能可贵的是,“他追求荣誉,却不贪恋荣誉。”靳祥生的部下陈扬回想起在内蒙古母杜柴登项目部时,“推举单位先进个人时,本来选定的是靳祥生,但是他却主动让给了我……”
不过是走过一座桥
采访的最后一天,该处党委书记倪木楠总结“靳祥生的奋斗经历,在当下很值得80后、90后学习。他能吃苦、爱学习、能奉献、爱钻研,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平平稳稳,踏踏实实,没有年轻人的浮躁”。
在与淮南处分管技术工作的处领导沈华军闲聊时,他又给记者透露几个细节,“小伙子脾气很好,甚至在批评他时,他也是乐呵呵的说,‘好好,我下次改,一定改’这么听话的小伙子都让你不忍心再说什么”,说着说着,沈华军又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一直都没有搞清楚,我还专门到他出事的那个路口去看过,路那么宽,根本就没有什么车……”
回忆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它会把你所有的悲伤倒腾一遍,再暴露一次。
回到合肥,晚上整理材料时,翻到他写的“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都将更加尽心尽责地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自己,与公司一起成长。”他已经没有将来了……心中倍加悲凉,想想他的事情,想想受采访人的表情,我时常需要凭眺黑夜,以平复激动。
当晚,我失眠了,想了很多事情,关于生死、关于人生价值、关于活着的意义和人的精神。想起一句话,它来自一本叫《相约星期二》的书:“死亡不过是走过一座桥,到远方去旅行,肉身是无法永恒的,永恒的是人类的精神和爱。”
躲不过那个“十字路口”,但是他走过了一座桥。
关山风寒,塞北雪冷,这次回到老家好好休息吧……